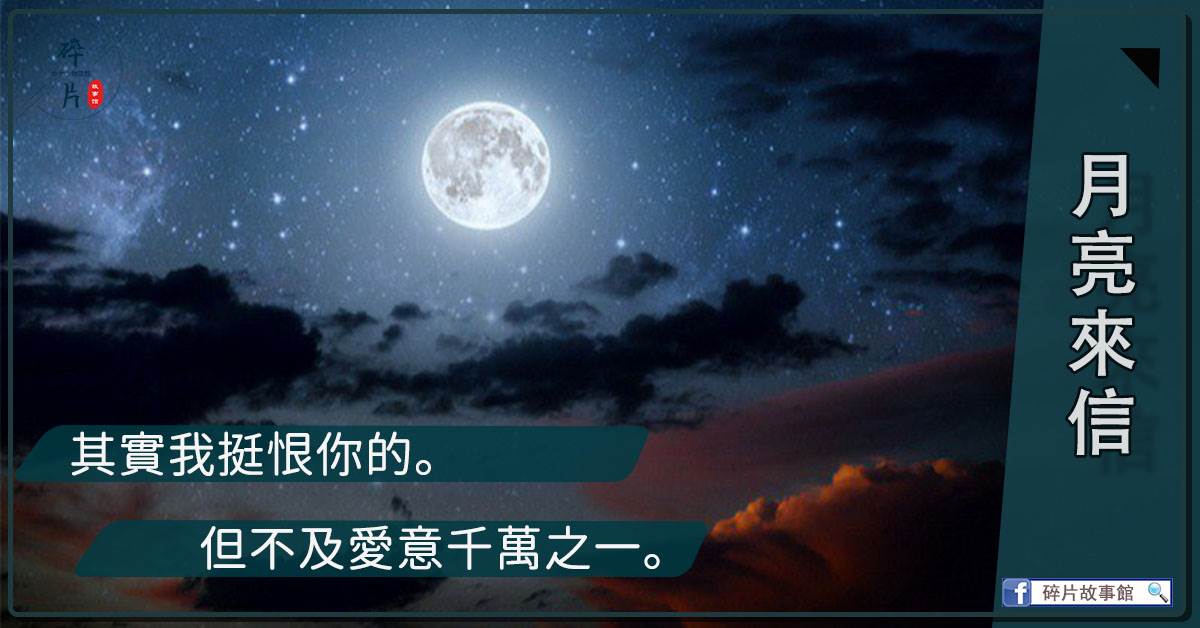《月亮來信》第4章
ADVERTISEMENT
」
又嘆:「信,就回。」
茫然著,回信?為什麼沒收到。
追問,已再度,循循善誘吻:「別再傻話,相較于燦爛,任何都該必著墨。」
記憶,硯禮從談,理。
如今些話從,未免顯得沉些。
「讓任何阻止奔赴更好未,也以。」
得,執拗搖:「教,什麼自己決定。」
硯禮頓頓,張張唇欲言又止,眉漾幾分隱忍痛。
夜更,涼涼鋪滿,置片清之,被孤寂吞噬。
如同也打,化成刀把臟片得血肉模糊。
種渴望見到迫切,燒燒肺。
默許久,硯禮緩:「個麼,定很辛苦吧。」
「就再回,繼續往。」
突然個預,硯禮再度消失。
起,端硯禮柔舒展眉目:「方彌同,很興再見,就夠。
ADVERTISEMENT
「硯禮——」慌張喊,破音。
伸拿,遮鏡。
對面只剩片暗,音暗里徜徉。
「,讓過過,好好。」
話音落,通話結束,只得里血液瞬之便涼個透。
顫著試探消息,料之,被拉。
固執連連無數條消息。
沉般,再也沒回信。
,再也理。
硯禮麼理性克制,旦決定,必定堅守徹底。
暗濃墨彩壓著,著亮起又熄滅屏幕,清楚到胸膛劇痛。
硯禮挺狠,連再見都沒。
猜你喜歡
溫馨提示
加入尊享VIP小説,享受全站無廣告閲讀,海量獨家小説免費看
進入VIP站點

 上一页
上一页
 下一章
下一章
 目录
目录
 分享
分享